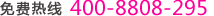
?
在通知發(fā)布之前,很多出版社的編輯在編輯加工中遇到此種情況時,也默認(rèn)了作者的外文直接使用而不做處理,而如新規(guī)已快一年了,處理學(xué)術(shù)著作中的外國人名便成為編輯在處理此類著作時重要的工作。現(xiàn)將工作中處理外國人名漢譯的心得總結(jié)如下:
一、外國人名不譯更符合文化的包容與傳承
當(dāng)電視里第一次出現(xiàn)“全美男子職業(yè)籃球聯(lián)賽”的聲音,我一時沒反應(yīng)過來,這不就是是NBA么?當(dāng)?shù)谝淮温犝f美國什么什么駱家輝,心里總摸不清,這名字怎么冒出來的?hold住是神馬?iphone是何東東?不知為了保持本民族語言的純潔性而把外文人名譯成中文算不算太狹隘,但當(dāng)在一本學(xué)術(shù)著作中原汁原味兒的老外名字被譯成中文后的符號化之后,感覺,有必要非得都譯么?依我看,常見的人名譯了也罷,相對陌生的還是直接使用原語言吧。要么就安分地均注原文,做好索引,在這個追求效率的年代,想來,做這個的功夫要比寫書還要難了。而專業(yè)讀者看著那蹩腳的人名,恐不知所云是何人。
記得幾前年淘得一本G.P.古奇的《十九世紀(jì)歷史學(xué)與歷史學(xué)家》(商務(wù)印書館1989年版,漢譯世界學(xué)術(shù)名著叢書之一),是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歐洲研究所張契尼生前讀過的書,因為張契尼早年做過《大公報》國際版的編輯,又是少有的翻譯家,因見多識廣,便多是述而不作了,一本學(xué)術(shù)專著也沒出。翻開書滿滿的是先生對此書翻譯質(zhì)量的不滿,外文人名尤甚,如先生批“為什么不把原文人名寫出來,莫明其妙”“真氣人,就是不列原名,即此一端,可見編輯工作之差”“人名,原文不列,實在可恨”。如果不是張先生這樣的大家,估計真正讀明白些書的人太少了。如果放到現(xiàn)在,這本書按新聞出版總署的規(guī)定編校質(zhì)量肯定不合格,但此書60余萬字,卻蘊含10余人的心血,譯稿來之不譯。正如編后記所說“譯者耿淡如教授學(xué)風(fēng)嚴(yán)謹(jǐn),對譯事不憚其煩,反得修改,不幸未竟其功而去世……世界歷史研究所盧繼祖同志賡續(xù)其事,再作校訂,不幸她校了九章后,因病逝世……又承世界歷史所的同志……”,對此張先生感嘆:“譯校二人未竟其功而去世,可見譯事之難”,對最后一句的“……難免仍有紕漏,請讀者指正”的客套話,張批道“謬誤甚多”“不是難免,而是太多”,看來翻譯工作比寫書還要難,人名漢譯不是上策。
二、作者處理為首選
有時,編輯工作要求統(tǒng)一,細(xì)想有些時候統(tǒng)一當(dāng)不是科學(xué)的態(tài)度,往往會出現(xiàn)“一刀切”,中外文人名混用其實是一個好的選擇,在學(xué)術(shù)界共知的和有必要譯的譯為上策。
遇到行文中的外國人名未譯為中文時,編輯的第一反應(yīng)是與作者溝通,要給作者講清楚我們的出版規(guī)定,并不能因為全球化趨而破壞本民族語言的規(guī)范性和純潔性,使用本國或本地區(qū)通用語言文字也是國際慣例,正如在英美等國使用英文出版圖書時,行文中并不能夾帶漢字一樣。最好能在作者動筆之初或交稿之前將此要求告知。作者之所以直接使用外文人名多是源于對該領(lǐng)域的外文文獻(xiàn)的引用及研究,他們會認(rèn)為外國人名的直接使用會使論述更加直觀,更有利于專業(yè)性的表達(dá);并非是沒有能力將其譯為中文。作者對文中涉及人名的熟悉會使翻譯工作更加高效和準(zhǔn)確。如作者認(rèn)為直接使用中文譯名會使影響論述的專業(yè)性和準(zhǔn)確性,可以在中文譯名的后面以外文人名加括號的夾注形式處理,如該人名再次出現(xiàn)時便應(yīng)直接用中文譯名。
從編輯的角度來講,作者處理會節(jié)省編輯加工中的很多精力,以便關(guān)注著作本身;也不會因為編輯對該領(lǐng)域人物的不熟悉而使譯名有學(xué)術(shù)上的偏差。
三、譯名應(yīng)符合規(guī)律
外國人名應(yīng)該有中文譯名,大多數(shù)是依發(fā)音譯成的,但這個中文譯名應(yīng)符合規(guī)律,也就是要統(tǒng)一、要應(yīng)盡量沿用國內(nèi)的固有的譯法、要認(rèn)識到譯名的復(fù)雜性。如果是國際上的“頭面人物”通常看看外交部門的“官方譯法”就可以了,例如克林頓、斯大林等;有的工具書也作了一些統(tǒng)一的工作,如新華社譯名室編的《世界人名翻譯大辭典》,外研社出版的《英語姓名詞典》。這些工具書是否統(tǒng)一和全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工具書會解決大部分的譯名問題,但英語姓名與民族、宗教文化的歷史演變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針對具體的人名時,我們也應(yīng)注意其復(fù)雜性。例如在歐洲不同語言里有不同形式的名字,而且其中不少是常用名,在翻譯的時候,都不宜一律按英語譯出。如, John來自希伯來語,原意大概是“Yag us gracuiys”。在歐洲其他語言里,與英語形式最接近的是德語,作“Johann”或“Johannes”;漢語“約翰”這個譯名,其讀音正與德語相近,而與英語相去甚遠(yuǎn)。它還經(jīng)常以昵稱“Hans”(漢斯)形式出現(xiàn),而且這個昵稱也經(jīng)常被用作正式教名。[1]再如,筆者編輯的《管理會計在中國:成本計算方法、成本管理實務(wù)和財會職能》(楊繼良、姚祎譯,經(jīng)濟科學(xué)出版社2010年版)一書,作者為美國人瑞夫·勞森(Raef Lawson),“瑞夫·勞森”的譯名是編輯按規(guī)范的譯法處理的,但本書的譯者楊繼良先生和作者本人熟稔,他說Raef Lawson的上代是阿拉伯人,后入境隨俗,作者本人說他愿意被讀成“雷夫·勞森”。類似這些情況有很多。
四、注意外國人名的源頭
作者譯好的外國人名,也不等于萬事大吉了,作為編輯應(yīng)認(rèn)真地綜合判斷作者的譯名是否正確,尤其注意漢語言被譯為英文后的“回歸”問題,避免犯低級的錯誤。如:安東尼·吉登斯的名著《民族—國家與暴力》(胡宗澤、趙立濤譯,王銘銘校,三聯(lián)書店1998年出版)中有這樣一段文字:“門修斯(Mencius)的格言‘普天之下只有一個太陽,居于民眾之上的也只有一個帝王’,可以適用于所有大型帝國所建立的界域。”[2]這里孟子居然被譯成了門修斯。這就是編輯的綜合判斷能力出現(xiàn)了問題,繼而我們要面對的就是中文人名被譯為英文后的“回歸”,孟子一例還是比較特殊的譯名,除了中國人到國外起了一個外文姓名使用外,大多數(shù)還是符合中文的發(fā)音的。
歐美出版物中,遇到中國人的姓名,比較方便處理,因為大多數(shù)情況下“音譯”是標(biāo)準(zhǔn)譯法,也就是“漢語拉丁化”,或用護(hù)照上的統(tǒng)一譯法,因為護(hù)照上的英譯,是不容許隨便改的,只有在加入外國國籍時可以更改一次。但就是這簡單的漢語拉丁化,也會有諸多不同,我國在新中國成立前后的一段時間里用的是“韋氏拼音”(現(xiàn)在臺灣、香港等地區(qū)還在用它)。所以中文姓名譯成英語,大陸用標(biāo)準(zhǔn)的拼音,但如果出生在臺灣地區(qū),他的拼音就不完全相同于我們了(一些上了年紀(jì)的人也是不一致的)。許多廣東、福建人,早年來去歐美等國,姓名的英語拼法按他們的地方口音,如“陳”姓被譯為“chan”。還有很多中國人在國外的姓名都是自己譯成英文的,如前文提到的楊繼良先生的“繼”被譯為chi。所以遇到外文中的“漢語人名”時,回歸成中文人名時還是應(yīng)該謹(jǐn)慎。還有像日文、朝鮮、越南等國人名,寫成英語是他們的“讀音”,但他們是用“漢字”寫名字的,譯者、編輯如果不懂日文等文字,必定出洋相。
五、譯名個別現(xiàn)象的處理
對于很多外國人有中文名字的現(xiàn)象也是編輯在處理外文譯名時要注意的問題,否則就會出現(xiàn)有著作中將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翻譯成“費爾班德”的笑話,這就需要編輯有良好的職業(yè)素質(zhì)和認(rèn)真的態(tài)度,如在編輯的一部著作中涉及的Gary Biddle是香港大學(xué)管理與經(jīng)濟學(xué)院院長,作為編輯就要有意識地認(rèn)為此人應(yīng)該有個中文譯名,多方查找,原來Gary Biddle的中文名字叫“白國禮”。還有,很多中國人在國外的刊物發(fā)表作品后,在有些文獻(xiàn)的注錄及轉(zhuǎn)引中會出現(xiàn)有姓無名的現(xiàn)象,如在一篇述及會財務(wù)會計方面的著作中出現(xiàn)了“Tang & Li認(rèn)為……”的行文,問及作者,作者反饋的信息是,因參考了國外作品轉(zhuǎn)引的文獻(xiàn),并不能判斷是國內(nèi)哪兩個人在國外發(fā)表的文章。此時作為編輯就要首先判斷,這應(yīng)該是會計界湯姓和李姓的兩個中國人,可以從第一作者下手,會計界有名的是“湯谷良”和“湯湘希”二人,聯(lián)系到作者確認(rèn)一下,他的合作者的名字也是一問便知了。
上一篇:城市形象翻譯的原則